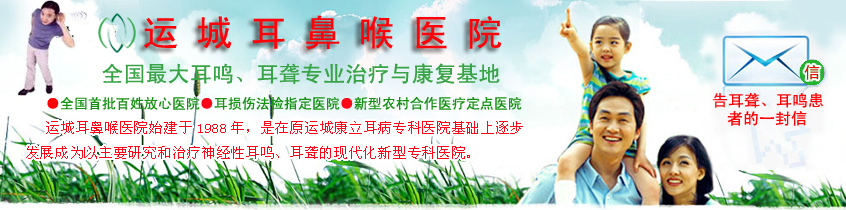杨 军 吴 皓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自身免疫性内耳病、特发性突聋、梅尼埃病、蜗性耳鸣、医源性感音神经性聋、Cogan综合征、遗传性非综合征性聋等内耳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仅在美国就有约3000万人患内耳病,65岁以上的人群至少30%有不同程度的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虽然国内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报道,但鉴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患者数可能要多得多。由于内耳在听觉和平衡方面的重要性,治疗方法不当可造成内耳生理功能不可逆性损害,以及其在解剖上的特殊性,即内耳结构微小、精细,不敢轻易扰动而造成的治疗手段的贫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耳疾病的治疗效果。目前配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是治疗许多内耳疾病特别是感音神经性聋的唯一方法。但是有一部分内耳疾病可通过药物治疗获得较好的效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安全、有效的给药途径,因为有些药物全身长期和(或)大剂量应用,其副作用是破坏性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同时,全身应用时药物-靶定位性差,由于血-迷路屏障的存在使这些药物在内耳中不能达到足够的浓度。所以,适宜、安全、简易的给药途径就成为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而鼓室内给药途径有较全身给药无法比拟的优点:(1)目的性强,药物-靶定位性好;(2)可避开血-迷路屏障,直接进入内耳;(3)外、内淋巴中药物浓度最高;(4)无全身副作用。虽然相对于药物直接注入内耳而言,鼓室给药并不是最直接的途径,但是如果药物能够过圆窗膜渗则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内耳疾病治疗的安全而有效的方法。圆窗给药治疗内耳疾病的理论基础是药物必须能够经圆窗膜渗透,在内、外淋巴中达到较全身给药后脑脊液和血液中高得多的浓度。
圆窗膜的结构与病理生理
圆窗膜是介于中耳和内耳之间的软组织屏障,位于中耳内侧壁,由3层结构构成,内、外层分别与内耳、中耳的黏膜相延续,中层为结缔组织。种间的变异主要在于圆窗膜的厚度,啮齿动物的最薄,人的最厚。人的圆窗膜厚度为70μm,不随年龄增长而改变。其外层上皮细胞内含有丰富的线粒体、粗面内质网和比较发达的高尔基复合体,上皮表面有微绒毛;内层上皮细胞连接松散、基底膜不延续可允许跨膜的物质转运,细胞表面的较长的突起,内含无定型物和胞饮小泡等一些具有吸收功能的结构,提示除了释放机构能量和(或)将声波传导至鼓阶的功能以外,圆窗膜还可能参与一些物质的分泌和(或)外淋巴的吸收。圆窗龛的入口由中耳黏膜构成的皱折部分掩盖,称为假圆窗膜。已经有动物实验证实,圆窗膜为一半透膜,能够对杀菌剂、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局部麻醉剂、毒素、白蛋白等通透。包括水、离子、大分子(如毒素)和抗生素等一些物质都能跨过圆窗膜,每一种物质以不同的径路跨膜并被不同的因素所影响。渗透是有选择性的,影响渗透性的因素包括渗透分子的大小、浓度、电荷、圆窗膜的厚度和易化剂。
鼓室内给药的方法
从理论上说,由于鼓室内给药途径的独特优势,如果所用药物能够通过圆窗膜渗透,前述的一些内耳疾病均可治疗。就方法而言,已经报道的利用圆窗膜的渗透性治疗内耳病的给药途径有以下几种:(1)鼓膜穿刺注入药物,患者采取特殊头位(仰卧位,头转向对侧耳)使圆窗龛浸浴在药液中,方法较简单,但需反复由医师操作,药物注入后在鼓室内停留时间较短;(2)做外耳道鼓膜皮瓣,将微管引入鼓室,尖端置于圆窗龛内,微管与微泵相连,可根据需要间断或持续泵入药物;该方法可根据需要随时加药,医师和患者都可以控制时间和剂量,但需要全身麻醉以及手术;(3)鼓膜切开,在圆窗龛内放置泡沫凝胶或纤维蛋白胶,可通过滴药使其中的药物缓慢渗透进入内耳;鼓膜切开是耳科的常规操作,简单易行,泡沫凝胶使药物定点准确,只需患者自行定时滴药即可。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鼓室内给药治疗梅尼埃病
目前来讲,比较成功的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鼓室内给药治疗梅尼埃病,应用较早,历经近半个世纪,所用药物和用药理念也有演变。用于前庭治疗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有链霉素和庆大老素。1948年Fowler应用链霉素全身给药治疗眩晕,1956年Schukmect介绍了鼓室内应用链霉素治疗梅尼埃病。我们已经知道,前庭毛细胞对一些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链霉素和庆大霉素)较耳蜗毛细胞更敏感。这种耳毒性的差异使我们可以减弱前庭功能而保存听力,这就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治疗梅尼埃病的理论基础。Ⅰ型前庭毛细胞较Ⅱ型毛细胞对耳毒性的影响更敏感。较之Ⅱ型毛细胞,Ⅰ型前庭毛细胞的加速度反应具有更大的动态反应、更无规律、加速度更可变。由于家族易感性的存在,用链霉素后有些个体易致耳聋[1],逐渐地,庆大霉素代替了链霉素作为治疗梅尼埃病性眩晕的药物。一定剂量的庆大霉素可选择性地破坏壶腹嵴和椭圆囊斑的毛细胞,消除前庭的病理性兴奋;另外,庆大霉素可通过对产生部分内淋巴的前庭暗细胞的毒性作用,破坏其分泌功能,影响内淋巴液的生化环境,达到缓解膜迷路积水的目的。庆大霉素鼓室内给药治疗梅尼埃病被称为化学性迷路切除。应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治疗梅尼埃病的目的是减少发作或减轻旋转性眩晕发作的严重程度。在破坏性的手术如前庭神经切断术后,平衡失调、特别是在快速的头部运动时仍然可存在如初。从理论上说,前庭神经切断术去除了梅尼埃病患者波动性的前庭传入冲动,从而抑制了眩晕的复发,但术后可断发急性或慢性平衡失调。庆大霉素鼓室内给药治疗梅尼埃病可选择性地减少眩晕的发作而不更多地影响前庭功能的静态成分。如果另外1耳以后发展成梅尼埃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例如老龄化)前庭功能下降,那么残余的前庭功能就非常重要。通过重复用药来精细调节单耳的前庭功能是鼓室内用药(相对于外科手术独具的优势。)
由于所用庆大霉素的剂量、鼓室内给药的方法以及眩晕控制的评判标准不同,各家报道的结果不尽一致,但庆大霉素鼓室内给药治疗梅尼埃病的临床效果是确定的。Monsell[2]等报道鼓室内应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治疗梅尼埃病,眩晕控制率为86%-93%,听力保存率为55-70%。Lange[3]报道通过鼓膜通气管注入庆大霉素治疗92例患者,90%眩晕控制,而24%听力进一步下降。可以看到,眩晕控制率令人满意,但部分患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力损失,虽然许多报道说眩晕控制后的梅尼埃病患者较少抱怨听力的进一步下降。近十年来,庆大霉素的用药理念有了变化,从过去的化学切除(chemical ablation)逐渐演变为化学改变(chemical alternation)[4,5]。化学切除能够非常成功地控制眩晕,但以损失耳蜗功能为其代价,而化学改变控制眩晕的效果不如前者,但影响听力的机会较少。鼓室内给药的方法亦不同:固定剂量(化学切除)或滴定(化学改变)。前者是采用预先确定的固定的剂量、时间给药直到计划完成或副作用出现;目前许多作者提倡应用滴定技术,即为达到一特定的目标点(眩晕控制及听力损失),将药物逐步滴入,治疗过程中重复作听力和前庭功能检测以指导滴定。其目标包括冷热空气的眼震电图检查结果出现100%前庭反应降低而不产生听力损失。两种方法比较,眩晕控制率相似,但接受固定剂量治疗的患者听力损失的水平明显高[6]。Blakley[7]复习了18篇报道鼓室内庆大霉素给药的文章,眩晕控制成功率为77%-100%,有0-75%的患者出现耳毒性所致的听力损失(平均为30%),听力损失出现多依赖于给药的方法(化学切除或化学改变),而受庆大霉素的浓度和给药方案的影响不大。Jackson等[5]推荐的方法是庆大霉素浓度10mg/ml,滴药后患耳朝上仰卧15min,每日3次。每周测纯音听力(气、骨导)、言语识别率和平衡功能(冷、热空气眼震电图),并询问患者有关眩晕、耳内胀满感、耳鸣和平衡失调等的主观症状。治疗是否继续依赖于客观检查结果和患者的主观症状。治疗时间通常为2-3周。几周后若未达到100%前庭反应降低、仍有平衡失调,治疗应当停止。如果治疗期间听力显著下降(纯音听力下降≥10dB或言语识别率下降≥15%),可用类固醇激素挽救听力[5]。强地松60mg/d,2周,然后逐渐减量。12例听力显著下降的患者中,9例(66.6%)恢复到治疗前水平。口服或与庆大霉素一同鼓室内给予类固醇激素,结果同样令人鼓。
类固醇激素鼓室内给药治疗免疫介导的内耳疾病
另一引起广泛关注和具有良好前景的通过鼓室内给药治疗内耳病的药物是类固醇激素。目前,国外已有较多关于利用圆窗膜对药物的渗透性来治疗内耳疾病的研究报道,但大多还仅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并未成为临床治疗内耳疾病特别是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常规手段。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包括基因性和非基因性效应,前者是通过作用于内耳的受体而起作用,后者是一种化学机制。Rarey等[8]检测了1例死于巴金森病的人内耳组织,发现类固醇激素受体广泛分布于内耳,其中耳蜗多于前庭,而耳蜗中以螺旋韧带最多,Corti器和血管纹居次,与大鼠耳蜗中的分布类似。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有:(1)与受体结合导致特异性基因表达或转录的改变;(2)影响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代谢,从而导致特异性mRNA数量增加;(3)影响细胞渗透压;(4)干扰许多不同的与浆膜有关联的过程,包括跨膜离子流,并影响参与氧化磷酸化酶的活性[9]。另外,Yao等[10]检测到地塞米松给药后有内耳蛋白的重新合成,说明这类药物通过代谢酶的蛋白质合成调节在内耳细胞代谢的监控中也起一定的作用。
类固醇激素鼓室内给药治疗有效的疾病主要是免疫介导的内耳疾病。1979年McCabe首次报道了自身免疫性感音神经性聋,此后20多年来,包括自身免疫性内耳病、特发性快速进展性双侧神经性聋、自身免疫性前庭耳蜗疾患、免疫介导的双侧梅尼埃病等一类由免疫介导的内耳损害所致的疾病或症状群陆续被报道[11,12]。由于这类疾病是临床上导致严重的耳聋及前庭功能损害的常见原因,其发病机理和治疗受到日益重视。目前已经公认,内耳并非为一免疫豁免器官,其受全身免疫系统的监视,血液中低水平的抗体和淋巴细胞可以穿过血-迷路屏障,引起免疫和炎症反应。免疫介导的内耳疾病由免疫介导的发病机理,使得长期以来免疫抑制,包括类固醇激素及细胞增殖抑制剂成为治疗这类疾病的主要方法。Chandrasekhar等[13]证实鼓室内注射地塞米松1h内,外淋巴中就可达到远较全身给药后高得多的药物浓度。Parnes等[14]的试验也证实,鼓室内分别注入地塞米松、甲基强地松龙、氢化考的松后不同时间点(1、2、4、6h)内、外淋巴中的药物浓度均高于全身给药。其中,鼓阶外淋巴和前庭阶外淋巴中3种药物的浓度相似;内淋巴中的药物水平总高于外淋巴。
关于类固醇激素鼓室内给药治疗免疫介导的内耳疾病尚有争论,有报道说地塞米松、强地公及免疫抑制剂如环孢霉素局部应用都不能减轻免疫介导的听力损失,而报道有效的文献也不在少数。Chandrasekhar等报道鼓室内注射地塞米松后使圆窗浸浴在药物中20min治疗突发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取得了满意的效果。Kopke等[16]报道经引人鼓室内、尖端(直径1.5mm或2.0mm)插入圆窗龛的微管持续(10μL/h,14d)泵入甲基强的松龙治疗突发性感音神经性耳聋,并认为这种方法较单纯鼓室内注射药物的效果更好。Parnes等[14]报道经鼓室内注射类固醇激素治疗,37例患者各类内耳疾病的患者中包括突发性耳聋、Cogan综合征、自身免疫性内耳病、手术致聋等在内的13例听力得到改善。Jackson等[15]介绍能够耐受全身类固醇激素治疗的患者首先用口服类固醇激素,如2周后没有完全恢复,则开始用鼓室内给药治疗。有类固醇激素禁忌证如糖尿病、高血压、消化道溃疡或免疫缺陷病的患者可直接鼓室内给药以避免药物的全身副作用。地塞米松4-24mg/ml,3滴,每日3次。2周后测听力,如听力有反应但未完全恢复可再用2周。
从目前情况来看,与庆大霉素鼓室内注射治疗梅尼埃病不同,类固醇激素圆窗给药治疗IMIED并未成为一种常规的、被广泛接受的临床治疗方法。Blakley等[17]认为鼓室内类固醇的应用仍应进一步研究。这也是目前达成的一般共识,因为有关局部给药的许多问题并不十分明了,如类固醇激素的选择、局部给药的具体策略——鼓室内注射抑或微泵给药、药物剂量、给药时间等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积累数据。但利用圆窗膜的结构和功能的特点经这一中耳与内耳之间天然的半透膜给药治疗免疫介导的内耳疾病有较全身给药无法比拟的优点,动物实验和临床结果显示它将成为一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法,并会为越来越多的耳科医师关注和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
除免疫介导的内耳疾病以外,还有报道认为类固醇激素鼓室内给药能够明显减轻急性前庭性眩晕患者的眩晕症状以及改善蜗性耳鸣的症状。
经鼓室-圆窗膜的基因治疗
遗传性聋的最终治疗依赖于对其突变基因的修正,耳蜗基因治疗则是遗传性聋惟一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经鼓室内给药(渗透微泵、耳蜗内直接微量注射或将浸有载体-基因复合体的明胶海绵与圆窗膜直接接触)是基因治疗载体进入内耳惟一便捷有效的途径,能够用少量的载体材料获得较高的靶器官浓度而使对非靶器官的泄露减少到最低程度。基因治疗在耳聋防治方面的实验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建立准确的耳聋疾病动物模型,选择目的基因和适当的载体,外源性基因表达的可控性以及载体及外源性基因导入的安全性等。随着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和耳聋基因病学研究的日新月异,相信不久的将来,人类耳聋基因治疗一定也会造福于广大耳聋患者。
参 考 文 献
1 Higashi K. Unique of steptomycin-induced deafness. Clin Genet,1989,35:433-436.
2 Monsell EM, Cass SP, Rybak LP. Therapeutic use of aminoglycosides in Meniere's disease. Otolaryngol Clin Noth Am,1993,26:737-746.
3 Lange G. Gentamicin and other ototoxic antibiotics for the transtympanic gentament of Meniere's disease. Arch Otorhinolaryngol,1989,246:269-270.
4 Harner SG, Driscoll CL, Facer GW, et al. Long-term tollow-up of transtympanic gentamicin for Meniere's syndrome. Otol Neurotol,2001,22:210-214.
5 Jackson LE, Silverstein H. Chemical perfusion of the inner ear. Otolaryngol Clin North Am,2002,35:639-653.
6 Toth AA, Parnes LS. Intratympanic gentamicin therapy for meniere's disease: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f two regimens. J Otolaryngol,1995,24:340-344.
7 Blakley BW. Update on intratympanic gentamicin for Meniere's disease. Laryngoscope,2000,110:236-240.
8 Rarey KE. Curtis LM. Receptors for glucocorticoids in the human inner ear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1996,115:38-41.
9 Lamm K, Arnold W. The effect of prdenisolone and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agents on the normal and noise-damaged guinea pig inner ear. Hear Res,1998,115:149-161.
10 Yao XF, Buhi WC, Alvarez IM, et al. De novo synthesis of glucocorticoid hormone regnlated inner ear proteins in rats. Hear Res,1995,86:183-188.
11 Stone JH, Francis HW. Immune-mediated inner esr disease. Curr Opin Rheumatol,2000,12:32-40.
12 Rahman MU , Poe DS, Choi HK. Autoimmune vestibulo-cochlear disorders. Curr Opin Rheumatol,2001,13:184-189.
13 Chandasekhar SS, Rubinstein RY, Kwartler JA, et al. Dexamethasone pharmacokinetics in the inner ear: comparison of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and use of facilitating agents.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2000,122:521-528.
14 Parnes LS, Sun AH, Freeman DJ. Corticosteroid pharmacokinetics in the inner ear fluids: an animal study followed by clinical application .Laryngoscope,1999,109:1-17.
15 Chandrasekhar SS. Intratympanic dexamethasone for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clinical and laboratory evaluation. Otol Neurotol,2001,22:18-23.
16 Kopke RD, Hoffer ME, Wester D, et al. Targeted topical steroid therapy in sudden sensorineural hesring loss. Otol Neurotol,2001,22:475-479.
17 Blakley BW. Clinical fornm: a review of intrarympanic therapy. Am J Otol,1997,18:520-526.
18 Lalwani AK , Jero J, Mhatre AN. Current issues in cochlear gene transfer. Audiol Neurootol,2002,7:146-151.
19 雷雳,韩德民.耳蜗基因治疗的实验研究.韩德民,主编.2002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新进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658-668.
(摘自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2004年12月第39卷第12期)